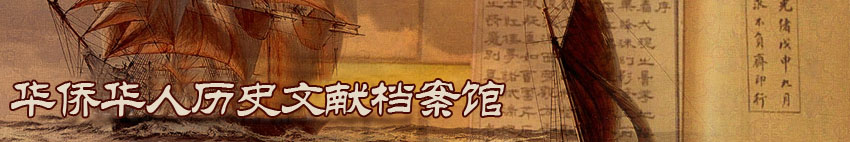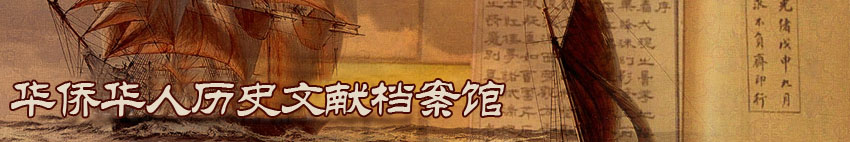梁启超 光绪皇帝 康有为---戊戌变法(钟卓安)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的确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绪皇帝究竟是维新皇帝还是洋务皇帝?第二,康有为有没有背弃自己的变法纲领?第三,怎样看待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揣冒昧,准备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刍荛之见,以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一、年轻的维新皇帝范文澜同志说得对:“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4页。)光绪皇帝究竟接受了哪些新思想?想有什么样的作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光绪皇帝在位三十三年,但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不过是当中十年,其中能给历史留下比较深刻足迹的又是戊戌百日,其他时间他都是以默默无闻的傀儡身份度过的。因此,评价光绪皇帝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戊戌年他和康有为等维新派合作推行的百日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张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务派的皇帝。
(一)在政治方面,他们说,作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皇帝而是洋务皇帝的最主要根据,是康有为的开国会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而设制度局的建议最后也是“石沉大海”。的确,开国会、立宪法和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变法主张的、纲领。但是应该说明,在百日维新的初期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康有为突然改变了主意,基本上放弃了自己坚持多时的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因此一般地说,不存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上谕有没有反映康有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的问题。而特殊地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也仍然准备采纳其他维新派如谭嗣同、林旭等开议院、立宪法的建议,使变法维新向前跨进一步。(见杨锐:《与弟省严书》,《觉逸要录》卷四,第17—18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8—159页。)据梁启超说,时大学士孙家鼐以“君权从此替矣”来警告光绪帝,要他放弃议院说;光绪帝答曰:“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以后,只是由于康有为等人以“民智未开,守旧太多,开议院则益阻挠新政”相劝,反对急行议院,光绪帝才暂放弃开议院、立宪法的打算。但直到此时,光绪帝也没有抛弃开议院、立宪法的念头,只是说“待后数年乃行之”,改日再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14页。)七月二十七日(以下均指旧历)的上谕还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戊戌变法资料》二,第64页。)继续流露出要仿照西方,“为民立政”,改良中国政治的意向。显然,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上谕中“只字”不提议院和宪法,并不表明他拒绝维新派的纲领,和维新派“同床异梦”。
至于制度局,十分明确的事实是,康有为始终坚持,而光绪帝也力争实行。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面陈述。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人们在谈论制度局的时候,往往是第一,忽视了康有为建议设制度局的《上清帝第六书》为什么经历了五、六次上来下去的反复之后才被实际作罢的原因;第二,把制度局和懋勤殿分开,以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奏陈《第六书》,由于礼部尚书许应□“攻击于恭邸前”,因此“抑压迟迟,至二月十三日(应为十九日)乃上”。时,翁同□不但同意开制度局,而且还想让康有为“直其中”(《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41页。)。但因关系重大,且“知西后之相忌,故欲借众议以行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第71页。),光绪帝“按例”谕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恃西太后势力,直至五月十四日才议奏,并全盘否定了奏折。十六日,光绪帝再令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二十五日总理衙门议复说,“事关重要”,必须派王大臣会议。光绪帝“益怒”,即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又拖了二十天,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等具奏,干脆以各式各样的名义把康有为《第六书》的建议几乎化为乌有,其中制度局一说变得面目全非。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联合抵制下,光绪帝被迫迁就退让(以上具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9、10页和《戊戌变法资料》二,48页的有关奏折和上谕。),使康折“成为虚文”。为什么会这样?康有为自己说得很明白:“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从王(文韶)言,遂定议。”(《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3页。)很显然,军机大臣们是在同光绪帝作合法斗争,用软刀子来扼杀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张,因此表面上对康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实际上偷梁换柱,予以否定,使“上亦无以难之”。无可奈何的光绪帝,只好让他们的“议复”意见“奉旨允行”(《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4页。)。事实很清楚,“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帝皆嘉纳之。然以见制西后,无权不能剧行,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清鉴辑览》,卷26,第10页。)光绪帝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以西太后为靠山的军机大臣们同样藐视了他的意图。虽然这样,但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设制度局的主张,直到百日维新的几乎最后时刻,仍然企图“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把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处所,向反对派进行“合法”反击。懋勤殿——制度局,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心目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因此,以制度局没有居为现实,就断言绪帝“否定”了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张,无疑是不恰当的。
(二)在经济上,论者否定光绪帝上谕维新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各级商务局的人选排斥了“普通商人”,二是“拒绝”了康有为裁撤厘金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根据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诚然,洋务派主张由“员绅”来主持农工商务,发展本派系的经济实力,光绪帝的上谕也多处表述了由“员绅”来“试办商务”的意见。但是,这并非光绪帝上谕有关发展民族经济的全部思想。第一,上谕说,这些“员绅”必须是“通达商务、明白公正”的人,不是凡“员绅”即可。第二,所有这些督抚和“员绅”的职责,在于“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0页。),“总期连络商情,上下一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20页。),“官民一气”,发展农工商业,而不是其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7页。)第三,鼓励商办实业,保护商民利益。当时,宋伯鲁认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7页。),杨深秀请求“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3页。),王文韶也汇报说广东华侨商人张振勋决定在烟台创办“酿酒公司”(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9页。),等等,对这些,光绪帝通通表示支持和鼓励,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情况见上页⑥⑦和本页①上谕。),并且还就中国商务之大宗——丝茶业的生产,提出,“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的建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0页。)五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更是明确指出:“近来各省商务,未见畅兴,皆由官商不能联络”,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并严禁胥吏勒索等弊”(《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8页。)。第四,规定凡创造发明,除予奖励外,还就“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兴造枪炮各厂”者,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1页。)。连枪炮都允许民间经营制造,“专利售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光绪皇帝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决心?难道这也是光绪皇帝相同于洋务派的地方吗?以上各点,都说明百日维新中关于经济政策的上谕,绝不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仅以某些经济机构的人选来判断光绪帝经济政策的性质,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妥当的。
至于康有为的裁厘建议,这倒确实没有在上谕中得到只字反映,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断定光绪皇帝“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康有为上奏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要求光绪皇帝能够一本“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但也正如康有为所言,厘金“岁入千五百万”,全国“不下十万人,皆仰食于此”(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如果一旦裁厘,不但使请政府本来就奇绌的财政更加拮据,而且势必将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驱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对裁厘这类大事不能不慎重从事,不敢贸然下令废之。不过,他毕竟不是顽固派,也不是洋务派,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尽管以“法称最善”一类的空洞词令对厘金“肯定”了一番,但通篇说的都是厘金之弊,主张进行整顿。(《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3—94页。)遍查百日维新所有上谕,没有一处直接反对康有为的裁厘建议,相反,据说康有为的裁厘奏折上递之后,“皇上览奏,恻然动念,面谕维新诸臣,谓行新政就绪,即决裁厘金。”可惜很快就因发生“八月之变,事乃中辍”(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知新报》第30册刊登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时加的注文。)。看来,说光绪帝在废除厘金制度问题上“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未尽合宜。
(三)关于文化教育。论者认为,“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而在这方面“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情况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说:不见得!应该说,百日维新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除了废八股改策论之外,还有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传统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深恶痛绝,按照康有为他们的本意,也是企图全部废除的,“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页。)只是考虑到顿然“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42页。)这样,无论康梁,还是光绪帝,都决定以废八股改策论作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入手。于是光绪帝屡下谕旨,一再申明:“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借法取士”(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上的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55页。);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8页。),等等。所有这些上谕,虽然没有搬用康有为奏折所说的“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的词句(《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11页。),而是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合呈的科举新章,决定乡会试均定为三场,并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光绪帝迎合了张之洞,反对了康有为,因为第一,上谕肯定的乡会试三场考试中,规定“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就所考内容和形式来说,同康有为的主张基本一致,不是什么“针锋相对”。第二,从上谕看,它既说要以“四子六经为根柢”,又说目的“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还把制义和策论并列,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态度的表现,但是在旧传统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敢于提出与之对立的新主张,这就说明新主张才是它的基本倾向,目的不是为了保旧,而是为了图新,“通经史”还是为了“达时务”。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带有调和色彩的上谕,其革新倾向仍然是明显和主要的,这又是与康有为相一致的地方。实际情况是,光绪颁的废八股、改科举的上谕,不但是为康有为所促成,而且几乎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主张。
应该说,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是百日维新中最卓有成效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新政。康有为认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康有为:《清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康论》上册,第286页。)当时《申报》也评论说:“此(乃)我中国由衰而盛、由弱而强之一大转机也。”(《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梁启超同样把它誉之为“维新第一大事”,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共兔园册子、贴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虽西后政变,改革失败,然“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为此,“骤失所业”的“愚陋守旧之徒”,“恨康有为特甚,到有欲聚而殴之者。”(梁启超,对光绪廿四年五月五日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5页。)此情此景,说明康有为正确,也说明光绪帝和康有为站在一条战线上。在谈到文教问题的时候,论者不该忘却百日维创办新学的主张,而正是这些主张最强烈地反映了光绪帝和康有为学习西方的意愿。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不止一次地下谕开办京师大学堂,命令各省府厅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中小学堂,各地义学、社学、乃至不在祀的民间祠庙,也通通改为学堂,而所有这些学堂都必须讲授官书局统一编译的“中外要书”,使“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这么一来,就将使中国构成大中小学组为一体的崭新的教育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近代教育新局面。这是改革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制的勇敢尝试和关键一步,它和废八股一起,给中国文化教育打上深刻印记,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可谓祛数千年之□□,俾学者之心顿有豁然开朗之一日也。”(《中外日报》评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七日。)也正因为这样,当时谣言纷纷,说是光绪帝服了康有为进的“药水”,“性情大变急,急躁异常”,竟“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皇上又入天主教矣”(苏维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37页。)。这无非是说光绪帝被康有为拉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看来,当时众人晓得,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是走在一条道上的人。
以上情况说明,光绪帝不仅在次要问题上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且在诸如事关官制改革的制度局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采纳了或准备采纳维新派的主张。如果光绪皇帝的意图得以实现,中国一定会出现不同于过去,也有别于洋务运动的新局面的。说光绪皇帝“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未免有失历史真实。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从主观上说,都希望中国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一番改革,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受人欺凌的境地,从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正是爱国救亡的宗旨,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更是变法维新的实践,使光绪皇帝由一个封建帝王“变成维新元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5页。),康有为成了维新领袖。百日维新的出现,少不了康有为,也离不开光绪帝,缺一不可,否则告吹。犹如一列火车,光绪帝是司机,康有为则是“顾问”(指挥),他们的目标是开往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但刚刚启动就出轨,车毁人亡。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列火车的标志是“洋务运动”,而是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所不容许的“维新变法运动”。正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势力的破坏和镇压,才使百日维新曲折和迅速夭折。百日维新的惨败,又从反面告诉我们:光绪帝和康有为一样,并不是什么洋务派,而是维新派。容□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容□:《西学东渐记》,《戊戌变法资料》四,第226页。)光绪皇帝是清朝十二个皇帝中,唯一值得后人崇敬的追求进步的皇帝。
二、康有为没有背弃自己的纲领,近来,有同志在把百日维新中的光绪帝打入洋务派行列的同时,进一步把康有为一派人物,也贬斥为“新洋务派”,说:“百日维新中,载□很少接受改良派变法的实质性建议,而改良派在实行君主立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两个主要方面,也根本没有实行自己的纲领”,“在关键问题上与洋务派一致”。关于载□在百日维新中的表现,上面已经叙述。在此仅就有关康有为的“两个主要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第一,关于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诚然,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是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政治□野所在,它关系重大,牵涉到后人对维新运动性质的评价。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康有为本来是态度十分明确的,早在戊子年(1888)就说要“祈取”“邻人”的专门之学——西方民选的议院制度(康有为:《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康论》上册,第48页。);以后又在《公车上书》中主张“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均由民选“议郎”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论》,上册,第135页。);《上清帝第四书》除直截了当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外,再次提到民选“议郎”的问题,且要求“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康论》,上册,第150页、158页。);《上清帝第五书》请皇上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论》,上册,第207页。)。可是,打从戊戌一月的《上清帝第六书》起,又来了一个制度局说,百日维新中更有“开懋勤殿”说。有的同志断言:“从第六书起,所有开国会、行宪法的话,在康有为的奏折里,再也没有出现了”,他“一直倒退下去”,“亲手消灭了”同洋务派的界线。我们说,康有为倒退是事实,但是并没有“背弃”自己开议院、立宪法的政治纲领,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线仍然是清晰可见的。据孔祥吉同志考证,属于康有为在被召见前夕替阔普通武代拟奏折(七月三日入军机登录档),继续要求“依照泰西设立议院”,“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内阁学士词普通武折》,《戊戌变未能档案史料》,第172页。)另据汤志钧同志考证康有为代宋伯鲁拟的《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四月二十九日),仍然希望光绪帝以“雷霆万钧之勇”,取泰西论政之“三权鼎立之义”,设立“专一论思之官”,“改制立法”,仿日本明治维新“特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草定章程,酌取宪法。”(《康论》上册,第262—263页。)这些大抵都是康有为在光绪帝四月二十三日颁定国是诏之后的开议院、立宪法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也对光绪帝说:“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对此,“上以为然”(《康谙》,《戊戌变法资料》囚,第145页。)。在这里,康有为虽然放弃了开国会的提法,但是他所说的“全变之”和“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又无疑含有制订宪法的意思。即使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波兰分灭记序》中,也还流露出康有为要求立宪的思想,他说如果现在“开制度局以变法,……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而不许者矣。”(转引自孔祥吉:《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看来康有为在戊戌年放弃设议院、立宪法的主张,是在他被光绪帝召见前后,而不是“在上第五书与上第六书之间”。对此,当事人康有为和事后与康有为形同水火的知情者王照,都有明确的说法(论者已详细引用),一般说来,他们没有必要把康有为思想转变的日程推后。当然,我们不怀疑康有为在戊戌正月初三于总署辩论之后,思想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更有理由相信康有为思想急剧转变和后退的契机,在于四月召见。在召见时,光绪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几乎全盘同意。“百闻不如一见”,召见时的这般情景使康有为真实地认为皇上“圣明”,更坚信变法必须依赖“君权”,所谓“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又能决开议院,授民以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页。转引自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155页。)按理,康有为应该趁势请求光绪帝开国会、授民权,但他但没有这样做,相反,改变了调子,把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搁在一边,而代之比较温和的设制度局和开懋勤殿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守旧势力强大,“守旧盈朝”,“旧党盈塞”(《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8—159页。),甚至有诸杀康、梁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253页。)在这恶势力面前,康有为害怕了、退缩了;第二,康有为本来就不相信人民群众,现在眼看自己挤进掌权者行列,脑袋顶天,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维新目标,因此以为暂放弃能为维新派争取更多权利的议院、民权说,不但是合适的,而且还可能带来养活维新阻力,使变法顺而易的效果;第三,相信能够扭转乾坤的皇帝,在条件成熟即所谓“民智”开通的时候,能够开议院、立宪法。这么一来,议会主张终于消失了,立宪要求也成为唧唧余音,为人不察。康有为把目光从开议院、立宪法,转注于设制度局和懋勤殿,当然表明他的变法思想在后退。但能不能据此就说康有为已经“背弃自己的政治纲领”?我们说:不能。在这里,关键在于弄清楚制度局、懋勤殿和议会说三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康有为曾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建议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数十人为修撰,派王大臣总裁,体制平等,俾得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制度新政,斟酌其宜。”并在制度局下设十二局,“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认为“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此外再“每道设一新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局”,以推行新政。(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故宫藏本。)以后更明确地说:“开制度局于内廷 ,妙选通才直,皇上亲临,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康有为:《为执行新政清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故宫藏本。)显然,在康有为的心目中,制度局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议会,初级上议院,或者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它由皇帝挂帅,由“通才”和王公大臣共同、平等地商讨国家大事,统筹全局,制定“典法”,然后颁施行,以实现“革旧图新”的目的。因此康有为说:“臣自去年(光绪二十三年)上书,条陈变法,其首重要,即在制度局”(康有为:《清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康论》上册,第351页。)。认为“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乘错,延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使。”(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书以助变□,请及时发馈,速筹全局,以免□肘,而图保存折》,故宫藏本。)而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计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构。这么一来,康有为他们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的主张,也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官制的方案,体现了维新派“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宗旨(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舍》,《戊戌变法资料》三,第21页。),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清朝政权机构的根本变革。正因为这样,康有为说“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六部内阁及督抚藩臬司道。……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3页。)对此,胡绳同志说得对:“很明显,康有为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545—546页。)
至于懋勤殿,这不过是康有为他们选拟的开制度局的处所,因此可以视之为制度局的代名词。康有为在拒绝阔普通武和谭嗣同、林旭等请开议院的时候,对此事说得很清楚:“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说:“上久与常熟议定开制度局,至是得诸臣疏,决意开之(指懋勤殿)。”(《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稍后,又在另一个奏折中重申:“伏乞皇上特下明诏,令群臣各荐才俊,府必一人,不问已仕未仕,概行征集阙下,大开懋勤殿,令入直行走,悬百国之图,备中外之籍,分列百政,各设专科,派以鸠集东西,斟酌古今,编纂政法,以备施行。”(康有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事折》,《康认》上册,第347—348页。),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为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地方,但在同治之后,只有南书房诸臣有进到殿“应制作书”。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和光绪帝都想以此为皇帝同康、梁等十大维新“顾问官”统筹新政大局的地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反对派的阻力。但还是由于顽固派反对、西太后不允,开懋勤殿虽“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竟未及开而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77页。)。因此我们说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不是矛盾的两码事,而是只有高低级别之分并且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从主张开议院,到改议院为设制度局、懋勤殿,的确反映了我们一再申述的康有为思想的倒退,但并不能据此说康有为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消灭”了同洋务派的界线。洋务派从来就没有主张实行议会制度或类似议会的制度,而是坚决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新与洋务,康有为和李鸿章,乃至光绪帝与西太后,他们在政纲上的界线应该说是清楚的。
第二,关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评判洋务派、维新派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时不能回避的又一个原则问题,但是我们不同意把它简单地当作评判是与非、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试金石。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反帝的人物和事件,固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然而不能倒过来说:凡是不反帝、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甚至心存幻想的人和事,都是一丘之貉,必须通通反对,一概撂倒。大家都明白,在共产党出世这前(或马列主义传入之前)的中国,那怕是激进的维新派如谭嗣同,或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缺乏本质认识的。在这方面,他们和康有为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上。就以据说即使变法胜利,也很可能被载□和康有为所“镇压”的激进的维新分子谭嗣同来说,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方面,也没有丝毫比康有为高明的地方,第一,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的表现,我们应该感谢帝国主义,如果进行反帝斗争,那就是不知感恩、不自量,到头来也只能自己找死(见谭嗣同:《仁学》卷下,《谭嗣同全集》第61页。);第二,主张把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大而寒□”的领土(据现在疆域统计,共约633万平方公里)分别出卖给英、俄两国,所得款项一用于对日赔款,二用于变法维新(见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407页。)。应该说明,谭嗣同的这些错误主张,从时间上说,比康有为的“卖国主义”还要早几年呢。
再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说,在接受共产党帮助之前,在反帝问题上,他和康有为一方面接受了物况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皆由(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变法”(康有为:《清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康论》上册,第261页。);是清朝“政体不好的原故”(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325页。)。都归罪于中国积弱,而不是去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另一方面,又都拜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为师,康有为从日、英仿制了君主立宪的蓝图,孙中山则从美国抄来了民主共和的方案,并都把这种蓝图、方案当作中国救亡图存、振兴发达的法宝。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康、梁维新派不但本质相同,而且表现也是极为相似的:康、梁把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看作至友和救星,孙中山也“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即第二个祖国(《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53页。);维新派主张对外让权借款以变法和中、日、英“合邦”,革命派则认为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利益,对外实行“门户开放”,以避免列强干涉和争取它们的援助,且同样“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三号,见《辛亥革命》二,第270页。)戊戌变法毫无反帝的实际表现辛亥革命也不过是一场反清革命,不敢进行反帝斗争,等等。他们的这些幻想,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产了,但是可怜他们又都没有及时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是只有共产党才懂得和才能总结的道理。在中国近代,反帝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简单地以此来标签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那么我们将很可能得出如此令人不能接受的结论:义和团比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进步,因为义和团的勇士都是爱国主义英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卖国主义”奴才;假若据此就说维新派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与洋务派达到了熔合一致”,那么孙中山等革命派又何尝不是这样?由此势必又从另外一条途径证明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和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脉相承,一个家族。事情终于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论者的反面。
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孙中山在接受共产党帮助之前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一样,也不能硬要康有为知道他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无法知道的事情,从而不做对帝国主义抱幻想的蠢事。作为后人,从前人身上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借鉴是应该的,但是过多和过严的指责却又是不必要的。如同分析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我们在比较康有为等维新派和李鸿章等洋务派性质的时候,必须首先注意到能够说明他们质的规定性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倾向,力求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洋务派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不要求也不愿意破坏旧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只是企图通过“局部修缮”来挽救和加强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一句话,他们对于“洋务”,要的只是体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而拒绝了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的精神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和制度,终极目的仅仅为了巩固大清封建统治,因此把这样的一个政治派别称之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把这个派别推行的洋务运动叫做“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可能更合适一些。而维新派不同,他们不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最主要的是主张改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一句话,终极目的是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是否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是区分洋务派和维新派性质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根据。因此,尽管维新派的表现是何等的幼稚,带有怎样的缺陷和错误,甚至有许多同洋务派相似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和洋务派有着本质的区别。维新派既不是如同洋务派那样的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不是什么半斤对八两的所谓“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就其基本方面和主要倾向来说,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派,由他们领导和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绝不是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我们相信,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已经照射在史册上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光泽,是不会黯然失色的。【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